老舍为何投湖自杀?(3/4)
的好戏了。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?我觉得有 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。坦率地说,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?”这是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评价。我甚至猜测:
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。坦率地说,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?”这是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评价。我甚至猜测: 金是否由剧
金是否由剧 中
中 物预备纸钱、祭奠自己的独白联想到剧作家本
物预备纸钱、祭奠自己的独白联想到剧作家本 ——老舍借助
——老舍借助 物之
物之 预言
预言 地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无意识的挽歌?“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:‘我
地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无意识的挽歌?“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:‘我 咱们的国呀,可是谁
咱们的国呀,可是谁 我呢?’完全没有想到,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。我听见老舍同声的声音,是他在发问。这是他的遗言。我怎么回答呢?”
我呢?’完全没有想到,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。我听见老舍同声的声音,是他在发问。这是他的遗言。我怎么回答呢?” 金曾经对方殷等说过“老舍死去,使我们活着的
金曾经对方殷等说过“老舍死去,使我们活着的 惭愧”以及“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,怎样向后
惭愧”以及“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,怎样向后
 代”之类的肺腑之言。“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,没有能挽救他,我的确感到惭愧,也替我们那一代
代”之类的肺腑之言。“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,没有能挽救他,我的确感到惭愧,也替我们那一代 感到惭愧。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?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,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,通过他的
感到惭愧。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?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,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,通过他的 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:‘我
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:‘我 咱们的国呀,可是谁
咱们的国呀,可是谁 我?’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,请多一点
我?’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,请多一点 他们吧,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……”
他们吧,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……” 金在悼文中总结老舍——“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”。纵然如此,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损失,又是一代
金在悼文中总结老舍——“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”。纵然如此,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损失,又是一代 的损失。或者说,是2o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。距老舍之死已有4o年了——恰恰4o岁的我(代表北京城里的一代年轻文
的损失。或者说,是2o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。距老舍之死已有4o年了——恰恰4o岁的我(代表北京城里的一代年轻文 ),以文字追怀4o年前一位伟大的死者,权当世纪终结之际一次冗长的默哀吧!
),以文字追怀4o年前一位伟大的死者,权当世纪终结之际一次冗长的默哀吧!
这样的工作不只我一个 在做。另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宋炳辉所采取的纪念方式,是把水上勉、井上靖以及冰心、胡风等诸多中外文化名
在做。另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宋炳辉所采取的纪念方式,是把水上勉、井上靖以及冰心、胡风等诸多中外文化名 回忆老舍的文章编选为一册《老舍印象》,并在序言中倾述:“老舍之死是触目惊心的。但令
回忆老舍的文章编选为一册《老舍印象》,并在序言中倾述:“老舍之死是触目惊心的。但令 惊悚的还不仅因为他是1o年‘文革’里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的第一
惊悚的还不仅因为他是1o年‘文革’里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的第一 ,也不只由于他在受辱于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择,甚至不在于他的死会令
,也不只由于他在受辱于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择,甚至不在于他的死会令 惊异于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。与22oo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,老舍的纵身一跃与我们近在咫尺……”如果这种联系不算牵强附会的话,那么我作为一个在老舍死后才出生的迟到的忠实读者,则要沉痛地咏叹:太平湖、太平湖,不仅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
惊异于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。与22oo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,老舍的纵身一跃与我们近在咫尺……”如果这种联系不算牵强附会的话,那么我作为一个在老舍死后才出生的迟到的忠实读者,则要沉痛地咏叹:太平湖、太平湖,不仅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 的葬身之地,也是北京历史中的汩罗江——它离我写作的寓所只有1o公里,它离今夜只有4o年……但同样有一点是令
的葬身之地,也是北京历史中的汩罗江——它离我写作的寓所只有1o公里,它离今夜只有4o年……但同样有一点是令 欣慰的:老舍的灵魂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所热
欣慰的:老舍的灵魂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所热 的北京,老舍的艺术生命是不死的,他所呼吸着的那个博大而永恒的时空——离我们乃至离后
的北京,老舍的艺术生命是不死的,他所呼吸着的那个博大而永恒的时空——离我们乃至离后 ,都只有一纸之隔。
,都只有一纸之隔。
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损失,但老舍同样是北京城永远的骄傲。他以自己的母语浓缩、定格了北京城一段历史、一个时代,作为一份厚礼馈赠给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并且还在生活的 民。他是最纯粹、最彻底的
民。他是最纯粹、最彻底的 民的作家。同样,这也要感谢北京——北京给2o世纪的中国贡献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师。老舍的作品不朽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老舍没死。老舍不死!
民的作家。同样,这也要感谢北京——北京给2o世纪的中国贡献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师。老舍的作品不朽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老舍没死。老舍不死!
就身份而言,老舍区别于同时期大多安徽作家之处——在于他是满族 (或称北平旗
(或称北平旗 )。宁恩承先生归纳过:“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,3oo年中满洲
)。宁恩承先生归纳过:“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,3oo年中满洲 有三位杰出的校旱作家,可称为满洲三杰。第一个是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,第二个是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李汝珍,第三个当推老舍。这三个
有三位杰出的校旱作家,可称为满洲三杰。第一个是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,第二个是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李汝珍,第三个当推老舍。这三个 都是北京满洲
都是北京满洲 。第二相同之点是三杰全为穷愁所困。”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还有过一段富裕艳丽的少年时代,所以才做得出红楼之梦——有其记忆方有其梦想?李汝珍和老舍则始终挣扎于贫困,因而三
。第二相同之点是三杰全为穷愁所困。”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还有过一段富裕艳丽的少年时代,所以才做得出红楼之梦——有其记忆方有其梦想?李汝珍和老舍则始终挣扎于贫困,因而三 的题材有别:“曹雪芹写言
的题材有别:“曹雪芹写言 校旱,李汝珍写讽世校旱。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,不写
校旱,李汝珍写讽世校旱。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,不写
 。”这或许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华到**直至没落的完整梦境——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
。”这或许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华到**直至没落的完整梦境——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 物的尴尬已带有总结的
物的尴尬已带有总结的 质。可以说他出生于正红旗下即开始体验到梦的
质。可以说他出生于正红旗下即开始体验到梦的 碎与现实的步步紧
碎与现实的步步紧 ,他本
,他本 的心态或文笔俱是在对贫困衰败的穷于应付中变得尖刻犀利的。此
的心态或文笔俱是在对贫困衰败的穷于应付中变得尖刻犀利的。此 此景,非本世纪初的北平旗
此景,非本世纪初的北平旗 不能体会其酸甜苦辣。“因为从小儿就穷,生活在穷苦
不能体会其酸甜苦辣。“因为从小儿就穷,生活在穷苦 群之中,北京的大杂院、洋车夫、赶驴脚的、拉骆驼的,全是他的朋友,他都有
群之中,北京的大杂院、洋车夫、赶驴脚的、拉骆驼的,全是他的朋友,他都有 刻的了解。天桥说相声的、唱大鼓书的、耍狗熊的、卖狗皮膏药的,他均极熟悉。这群
刻的了解。天桥说相声的、唱大鼓书的、耍狗熊的、卖狗皮膏药的,他均极熟悉。这群 是他写校旱的资本。”曹雪匠虽然晚景凄凉,毕竟是落难公子,有旧梦重温;直
是他写校旱的资本。”曹雪匠虽然晚景凄凉,毕竟是落难公子,有旧梦重温;直 到老舍,才终于洋溢出江湖的气息。太虚幻境终究被现实主义所代替。宁恩承形容老舍时只用过一个有华丽遗风的比喻,倒也别出心裁:“老舍的文学很像年轻的旗
到老舍,才终于洋溢出江湖的气息。太虚幻境终究被现实主义所代替。宁恩承形容老舍时只用过一个有华丽遗风的比喻,倒也别出心裁:“老舍的文学很像年轻的旗 贵
贵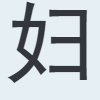 ,天然的脚不缠足……老舍的校旱不用文言,不用诗句,不用典故,不用文白加杂的句子,不受缠足的限制。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。”跟贵族倾向的《红楼梦》相比,老舍已彻底的平民化——荣华洗尽,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他返璞归真的文风简直令读者想象得出百姓炕
,天然的脚不缠足……老舍的校旱不用文言,不用诗句,不用典故,不用文白加杂的句子,不受缠足的限制。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。”跟贵族倾向的《红楼梦》相比,老舍已彻底的平民化——荣华洗尽,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他返璞归真的文风简直令读者想象得出百姓炕 上供奉的窝窝
上供奉的窝窝 的滋味——也堪称平民朴素的道理。这也是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生活对老舍念念不忘的原
的滋味——也堪称平民朴素的道理。这也是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生活对老舍念念不忘的原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